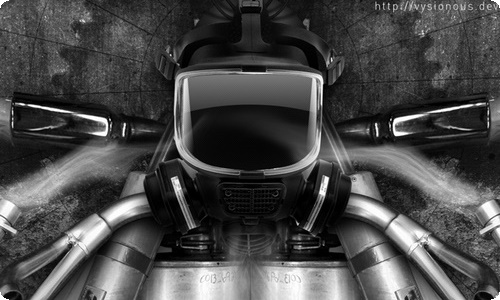端午的依赖散文
街巷很窄,雨停之后已经体会出凉爽。端午节给予北方足够的湿润,如同迟迟不来的春雨,一旦老天怜悯,结果淅淅沥沥下个没完。对季节的等待,应感激屈原,汨罗江不屈那天,注定给南北种下一粒牵挂,尽管遥远,却怎么也阻拦不住,要不然,不可能在冰雪城市的小学课本里,会传来哀怨的朗读声。
端午是地域的一种民众牵挂。楚地秭归的百姓一定是节制和温顺类型,隆中诞生聪颖人物,赤壁那场拼杀,几乎是由伶俐的大脑来完成。再看李时珍,用神农架的天然植物,来拯救病弱的人类,那些张狂的将士,面对手无寸铁的神医,不知相形见绌多少倍。反过来看移民的关东大汉,很难对应找到温文而雅的`昭君、毕升、董必武的原型。文武相对,在白山黑水间,一定会比拼个大头小尾。凶悍在北方,要占举足轻重的地位,比如说张作霖,霸道中充满机敏,再比如说杨靖宇和扬子荣,大义凛然,很少有人用清秀和忍辱负重形容他们,好象关东人的匪气曾与关东文化有关,连江河湖泊的名字,道出来都掷地有声,黑龙,这种只有在天际搏斗的神话才听说的事,竟然冠到了省份的头上,一直叫响到今天,不象汨罗江、黄鹤楼,赤壁,听起来都容易让人浮想联翩。在他们的茶余饭后谈吐间,楚地的山水人文,楼台庙宇,无不浸透和沾满神秘色彩和光环,由此使我们久居北方的人,很少在众人面前,夸夸其谈自己父辈光宗耀祖的一面,这是关东的悲哀和沉默。
共同面对盼望已久的端午,秭归的船夫,在兴高采烈涂刷龙舟这几日,两岸民众眉飞色舞,张灯结彩,而松花江的渔民,站在坝埂上,正为禁鱼和稻田浇灌而发愁,与其说追念汨罗江的逝水,不如说在江堤以外,民众对理想的期盼,对故人的思念,不同地域的人们,有着不一样的情愫。屈原的坚强,很大程度上,是北方人的一种寄托形式,端午,来到北方,是心灵的呼唤,犹如休闲的踏青,释放,流连,渐渐变成北方人的主题。
每次回头看端午,都会产生许多疑惑和感慨。与《楚辞》大相径庭,楚人太柔弱,太专注,汨罗江已经容纳不了膨胀的激情。本来一件古代哀痛的故事,让楚人年年演绎,已经完全改变原来初衷,这是楚人的聪明之处,重复,代数教程里枯燥无聊的叠加,被楚人拿来,变成自己千古传承的家训,成功地吸引不同肤色的人来膜拜。接踵而来的,早已忘记自己是外乡人,争相目睹不很宽阔的汨罗江,品尝洞庭湖的鲜蟹,登爬神秘的神农架,观无烟无火的赤壁。
楚人为自己的榜样而自豪,一个做梦都没想到以死抗争的老者,给他的后代和故土留下一笔丰厚的精神遗产。秭归的安静的祠堂,春阳从天井滴漏下来,老者们围聚在一起,他们不作声,吧嗒吧嗒吸抽着竹烟管,那些后背飘飞着大书包的年轻后生,一股脑踊进教室,倒背双手,张开大嘴,嗷嗷念诵《楚辞》的韵仄。
北方这个时候,老老少少早已向山里进发,他们每年都集聚在一起,步行的,骑自行车的,赶牛马车的,驾驶轿车的,浑身上下挂满晨露,急急忙忙朝山里奔的目的是,在太阳升起前,必须赶回家,将鲜香的艾蒿插在门上。老人在孩子梦醒之前,悄悄将五彩线系在他们的臂腕上。北方的端午清晨,是一派忙碌情景,比较端庄秀丽的楚地,再实际不过了。端午已成为崇高的默契,没谁千里迢迢赶到白洋淀采摘闻名的苇叶,但在这天的餐桌上,没有哪一家不津津乐道品尝必须的一道主食:粽子。
历来低调智慧的楚人一改矜持,走出秭归祠堂,划拨龙舟逆流而上,红旌耀眼,歌号冲天,向世人显耀汨罗江的气派。关东大汉照例不示弱,摩拳擦掌,率全家老小,走进绿色大山。端午弥漫北方有两种颜色,一种香包的大红,一种艾蒿遍野的大绿。汨罗江这天,老人眼睛里也闪烁两种色彩,楚国流动的鲜血,楚地的绿色山河,多么相似,流淌至今,仍旧乡音未改,掷地有声。